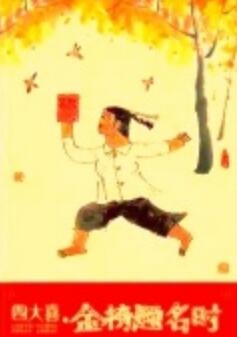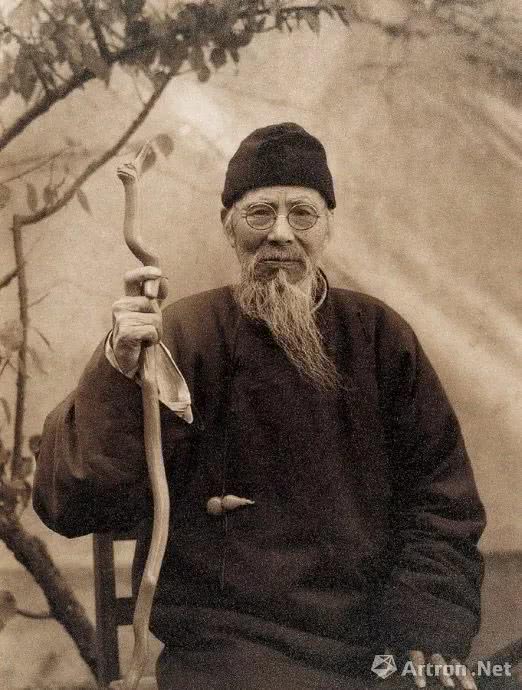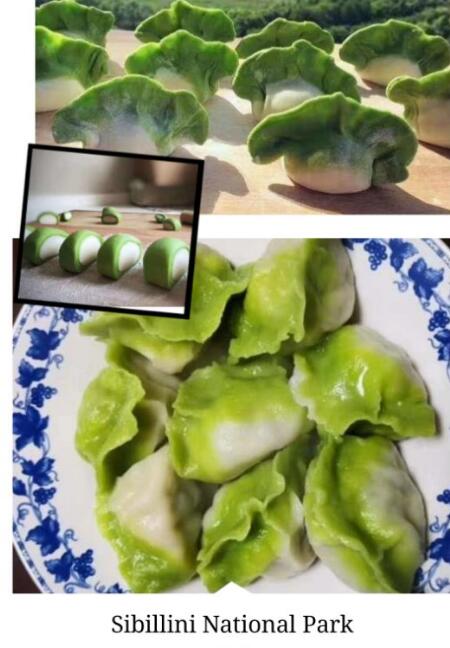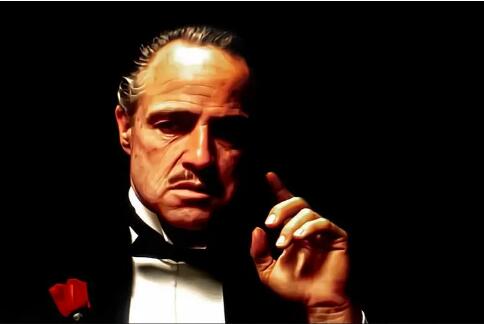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他们呐喊!——题记
有位作家曾这样描写七八十年代中国情景: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找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找拙朴的地方难。我想这位作家要是今天到农村去看看,就不会这样写了,至少看了我的家乡后就不会这样写了。以前也没有这种感觉,每年春节回到乡下小住几天,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这几年来,新农村建设搞得也还是挺好的,家乡这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确实也起了点变化,过年还能搞点文艺节目,也还很热闹呢。感觉乡村跟城里一样,有了点发展变化。
去年因老母病重,11月份我回了趟家,在家长住了一段时间,有20来天吧。这才让我感受到农村的寂寞,寂寞得让我窒息恐怖。感受到的另一面,却让我心里冰凉冰凉的。
我素来有早起的习惯。在家乡也是早晨起来,村前村后走走看看,到田间地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于农村的寂寞,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这20来天的常驻感受,还是让我十分的惊讶和难受。她的确也超出了我的想象。早晨在村子里散步,难得见到一个人,只有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和远处的鸟叫声。天天一个多小时的满村来回走,只有极少几天里,天气好时才碰到个把老人拄着拐杖到塘边来,透透新鲜空气,看看塘边的风景(水塘是村里最中心最开阔的地方,村人习惯聚集在这聊天凑热闹)。他们孤独地来,站在这儿孤零零地看景,看累了又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四周静静的只有老人的拐杖.戳地的嗒嗒声。
乡村的静是有些让人害怕的,到了晚上,村子里更是一片寂静。村里的小街小巷只有路灯在亮着,从6点30分到10点30分的四个小时里,在村子里散步,始终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蚊子的嗡嗡声,和偶尔蝙蝠飞过的声音。我这个喜欢清静的人,也被这憋得无法忍受。每晚都散不了几下步,就又回家陪老人聊聊天、谈谈地去了。但每次谈到这些,老人也总是叹气摇头,我又得要叉开这些话题聊点他开心的事,但聊着聊着又总会绕到这些事情上来。嗨,农村人谈农村事,总也绕不开这些的。
我本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只是这两年来随着年龄变大,人也变得怕孤独寂寞,也开始喜欢与人交际聊天啦,也总想在村子里碰到个清闲的人,特别是童年的玩伴发小,聊聊天叙叙旧。但我这个人又没有到别人家串门的习惯,再加上村人们的门,也是四时紧闭。父母又身体不好需要陪伴。其实,也只有偶尔空闲的时间,出来走走、看看,但确也常常因憋不住了而走出村到田野、茶园地头,走走看看。哎呀,那个静呀!让你憋得难受。别说和外面的世界比,就是和村里比,也让我心慌,村子里干干净净,也有几栋新房子,有点新农村的样子。而走出了村,走到田间地头,举目一望,只有村口附近极少数的一点点田地好像有人种过,但种田的人也是种中间的一点点田心了。到处的田坝及田间小道,已是荒得人们都难以通过了。到处都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儿时看到的那一片片良田、良地,也不知去了何方了,全是一片荒草。那记忆里的、修剪得平平整整绿油油的茶叶,也被杂草荒木所吞没。四周看不到一个做农活的人影。有时我也不禁问自己:那群不知疲倦日夜劳作的人群,去哪了?每天都这样憋闷地在村里村外来回踱步,有时候就想:农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啊哈,我这不是思考什么大事,我是闷得难受,憋得心慌;思考大事,轮不到我这样的小人物,我只是希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片良田良地,别荒废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有口饭吃吃。
写到家乡的寂寞,其实这只是轻描淡写。写深一点,是农村的孤独,农民的悲哀。每天带着这种心情,在村里散步,我的心里也总是沉沉的,每天都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走,希望能碰到一个能说话的人,希望能有个发泄的地方。一天,我好容易走到一片菜地,发现远处有个人在浇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喜。我就有点兴奋地走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是堂叔。我主动和他打招呼:
“叔叔在浇水了?”
“哦,是国全来家了。”堂叔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和我答腔道。
“叔叔,你歇会抽根烟吧。”我一边递烟一边掏出打火机。堂叔也一边接过烟,叼在嘴上,前倾着身子伸过头来,等我手里的打火机的火。我点着烟问道,“叔叔都七八十的人了,挑这么一大担水,挑得起吗?”只见他深吸了口烟,又缓缓地吐出,就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的。“挑不起呢,一次只挑半担,多跑几次就是了。”还没等我张口接话,老人就像打开了话闸似的,“你大弟二弟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你大弟媳到济南带孙子去了。”我赶忙抢过话闸答道:“那好哇,我大侄子到济南工作了?”叔叔又像和我争话说似的,没等我落话音就接话道,“是啊,一个在济南做事,一个在县中读书。你弟媳在济南带人,你婶婶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县陪读去了。你二弟的两个儿子,都在经公桥读书,你小弟媳也到经公桥陪读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老人了。”
老叔叔滔滔不绝地说着:“我要不做连饭都没得吃呀,行吗?”我赶紧接过话茬:“他们多少要管你一点吧?”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他们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搞点钱还不够小的读书呢。”“听说政府给我们农民也弄了社保,你也有点吧?”我问。老人又是长长的叹气:“50元一月能做什么用呢?喝水也不够呀。”我也长长地叹了口气。看着眼前这一片荒芜的田野,再看看年岁本不是很大却衰老得和年龄有些不大相称的老叔,我沉默了良久良久。“叔叔啊,可怜了你我这辈人呀,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可不是吗,年轻时拼着命种田,除了国家的集体的,剩下来的让你连饭都吃不饱。老天作孽呀。”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恨恨地把一勺水泼上老远。接着又挖一勺水,狠狠泼上远处,才放下,将勺子撑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说:“现在谁还在家种田,种出来的谷子连成本都不够,你还想指望他过日子?几十户人家一百六七十号人,在家的不到三四十个人,读书出去工作的不用说,就连几户在家种田的,也在县城买了房子,在那打份工,说是可以有份养老保险,老了有碗饭吃吃。村里除了有残疾最可怜的两户,子女全都在外面啦。”看着越说越激动的老人,我只有默默听着,不忍心打断他的话语。见他已不再激动,而是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是安慰还是劝导,突然又像是随口说出了一句话:“都出去了,这是好事呀。”老人像是被激怒了似的,狠狠地甩出一句话:“看以后吃什么?钱再多饭总要吃吧!”接着又狠狠地将一勺水泼向远处。
离开堂叔,走在曾经生机勃勃激情四射的沃土上,漫步于童年的梦幻中。可我眼前的田野,却是灌木杂草丛生、沟渠难辨一片荒凉。阵阵微风拂过我的脸颊,也摇曳着这片没边没际的荒漠杂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像是哀呜似的从我头顶掠过,飞向远处。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那句“钱再多饭总还要吃吧”总在我耳边缭绕。
看着前面一片冷寂的村子,回头看到还在劳作的堂叔,和远处躺在山坡上守望着这片荒凉土地的故人,我又想起了一生劳作却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的养父。
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栽禾班班长,年年带队栽禾班。年轻人带了一场又一场,可他一直在带队。每年早稻、中稻、晚稻要栽好几个月,是农业里面最累的活,可他栽了一辈子。到60岁时,因腰肌劳损,就弓腰驼背,无法伸直了。才70出头就辞世了。去的那天弥留之际,老人不停地指了指床头边的一衣箱子,好像在示意我什么。我打开箱子翻到衣服下面的一个小铁盒子,拉了出来问道是这个吗?他微微点了点头。我打开铁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裹着的布和纸,里面是一小沓钱。有100元,有十元的,有一元的两元的,集叠得整整齐齐。我数了一下有1850元整。我问他:“你是要这些吗?”此刻他已什么也不能回答了。我知道这是我平常给他的一点零花钱,和卖菜卖扫把积攒起来的钱。这也是他一生的积蓄。手捧着这布包,泪水止不住地滴落下来。他走时正是我两个女儿读大学时和我两次做手术的最艰难时期。每次给他的也只有十元五元的,他竟一分也没有舍得花,全积攒在这里。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想起我这可怜的养父,想起这一辈人的艰辛,我就泪如泉涌。但我又无可奈何。
农民这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这群让中华民族灿烂了几千年的一群人,似乎走刻了历史尽头。这群被陈毅元帅誊为,用独轮车推出中国華命的一群人,这个终曰辛勤劳作,确耍勤紧裤.带,为共和国典起强大工业的价级,今天确为生计不得不放下犁耙飘迫他乡。确没有人愿意去善待他们。
冬去春又来,但愿大地鲜花盛开硕果累累,但愿田野五谷丰登,人民丰衣足食。但愿这群可怜的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盼老天有眼,善待他们。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我,回到了那魂牵梦绕的小村子。站在曾经的小村口,望着眼前残破不堪一片废墟、空无一人的小村子,老泪纵横、失声痛哭。只有阵阵微风刮起尘土,落叶在漫天乱飞,只有天空飞鸟的哀鸣声。无人理会我这老汉的嚎啕大哭声,四周永远永远那么的寂静。
题外话——
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农民是这一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有人对他深表同情,有人对他幸灾乐祸不屑一顾。我敬告那些幸灾乐祸的没有良心的人,如果你们把他们逼得全都离开了故土,去背井离乡,那你们自己终将有日要自食恶果。农业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皮之不在,毛之焉附?
2019年3月写于南昌
作者:吳国全,南昌人,工程枝师,文学爱好者。
乡“情”相关文章:
★ 舌尖上的乡情
★ 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