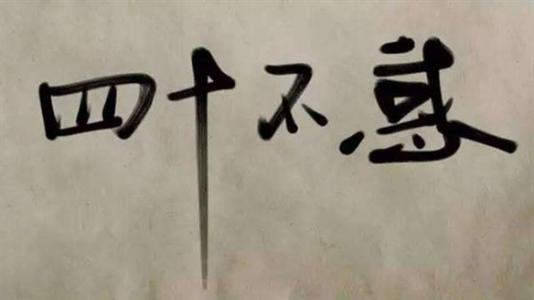《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
我的母亲,生于饥寒交迫的年代又饥寒交迫的家庭,家中共有5个兄弟姐妹,她是唯一的女子,虽是女子,但从未享受过女子的待遇,不是偏袒,而是除了虱子别的都有不起。每每谈到母亲的过去,她只是在叹息之余多说两个字——造孽。
父亲是随爷爷从别处搬迁而来,与母亲做了邻居,那个媒妁之言的年代,父亲占了近水楼台的先机。没有爱情,只有睡觉的窝、吃饭的锅。不得不羡慕我父亲,运气好到爆,捡了一块宝。由于母亲把过去进行了记忆删除,我也不想揭露她的伤疤,那我更多谈谈记忆中她的故事。
我的母亲,怀了十次孕。
1973年开始,我的母亲就有100个月3000多天在孕育,只为农村“传宗接代”。间隔最久的是三年,最短的是一年。从大姐的欢喜到三姐、四姐的失望,一直到我老七,全是“锅边转”。1990年在父母的第八次坚持耕耘下终于迎来“带把儿”的康康。康康的到来,母亲腰板挺直了,说话硬气了,父亲也脸上有了笑意,事业有了动力,我们升级为煤矿老板家的孩子,不仅有电视机、缝纫机、录音机,还能品味一毛钱三颗的糖、五分一条的白糖冰糕,五元一条的裙子,十元一瓶的麦乳精,二十元一套的春节订制套装,糖精泡饭、猪油抖饭更是可以随意吃到打嗖隔。
可惜,厄运专挑苦命人”。1992年,弟弟胸腔长瘤,父母耗尽家财四处求医,最终还是未能将康康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悲伤是什么,只知道母亲对着一个“小盒子”哭得撕心裂肺,责备“小盒子”是个狠心、无情的短命鬼。
将“小盒子”安置于山林,小小喘息一年,原本封肚的母亲再次孕育,总算在1995年43岁高龄时产下第十胎的弟弟,母亲这才结束生娃的前半生,开启另一段“百千万”历程......
我的母亲,养了百头猪,磨了千斤黄豆,做了万块豆腐。
弟弟出生后两年,煤矿产业不容乐观,家里一下子从“万元富”轮为“负万元”,父亲也变得低迷消沉。为了糊上九张嘴,还能到学校接受教育,母亲向邻居借了五十块钱,买了第一包黄豆启动创业。
连续十几年,我的母亲总是天不明地不亮开始做豆腐,直到公鸡打鸣数次还未收工。每锅豆腐用时两小时,全部卖出去可以赚两、三块钱。母亲的情绪也总是表现得很明显,有活干嫌活累,没活干莫名发脾气。直到自己当了母亲,我才理解她心中对金钱的焦虑。
做豆腐会产生很多豆渣,秉持不浪费还能多赚钱的原则,母亲开始养猪,与众不同的是,她养的猪和生的娃一样,比旁人多,从几头到最多的时候五十几头。我们割的猪草也从一背篓到几背篓,而我就是那个割猪草“拖皮撒胯”,“正事不做,豆腐拌醋”的叛逆女。母亲看到我经常都是“丧着脸”,动不动就说:“书读不走就不要克了,反正也交不起学费,天天在家把那电视机抱斗,上山把大背崖背斗算了”,不过从来都是嘴上功夫,很容易被右耳消化出去。相较于母亲的唠叨,父亲略显简单粗暴,武力解决干净利落,听不下去看不下去就是一棍子甩来,小时候鼓起勇气喊父亲,从来都是“爸爸,妈在哪?”
姐姐们背地里常说,母亲的“我觉得”和唠叨让她苦了、累了大半辈子。她觉得父亲不会养猪、觉得父亲不会干家务、觉得父亲对家庭不在乎,时常对着好吃懒做的猪毫无顾忌地“指桑骂槐”,十里之外都能听见她的咆哮和抽打在猪身上的鞭子声。而知趣的父亲从来不解释,只是默默的砌着猪圈和水井,一间又一间,一个又一个。其实我是理解母亲的,家庭压力的繁重,让母亲赌不起、输不起,生怕一个闪失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她将所有的情绪全部体现在不会反驳的动物身上,或许也是一种情绪寄托吧,只是方式选择不恰当而已。
如今母亲已七十古稀四世同堂,子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过得不错也还孝顺,可爬坡上坎都吃力的母亲因弟弟还未成家仍然放不下肩上的担子,猪还那么多,人还那么累,夜还那么熬。劝她跟儿女住,她说脏惯了,不适应。叫她把活放下,她说做惯了,闲不住。约她外出看世界,她说活多了,走不开。
这,就是我的母亲。大半生都在披荆斩棘,直到黄土淹到脖颈还在顽强拼搏的女人。

作者:陈敏,80后,昭通彝良人,文学爱好者,现供职于绥江县文化馆。部分作品见于《昭通作家》。
我的母亲,相关文章:
★ 东北行之一
★ 梦里水乡
★ 农民真幸福
★ 老宅的松柏树
★ 北湖的四季
★ 丑石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