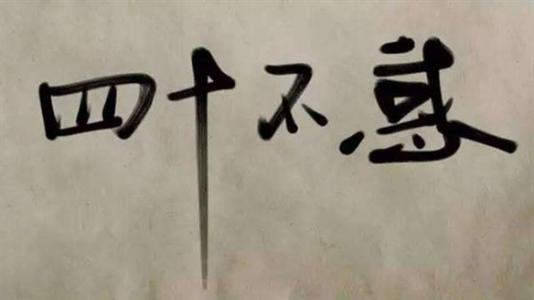读《张炜文集》随想
安玉琦
题记:《张炜文集》四卷本,《阅读的烦恼》《中年的阅读》《把文字唤醒》《难忘观澜》,“这是我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若是“从头看这大大小小的篇章,让我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我没按照先生的要求,从头看起,而是挑选着读起来的,不过越读越有趣味,喜不可言;而后便逐部逐部耐心读着,有点爱不释手啦;于是又精读了不少篇章,那种书香味道美极了。诚如先生所说:“比起用力编织的那些故事作品,这些文字好像更切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痛感。”的确,“这些文字是系列的短章编年,更是一部丝绺相连的心书……”读着,品着,也激起我心事涟涟,于是随想如下:
(一)
《爱小虫》里面说:“那时候我们不觉得小虫子之类是坏东西,它们当中的一多半是有趣和可爱的。”
比如虱子——它寄生人身上,喝人血吃人肉,可是我们也没觉着它们多么可恶,反而觉着很好玩。星期天,伙伴们在田野拾草或者剜菜差不多了,便找个避风、阳光又好的地方,脱下褂子拿虱子比赛,看谁拿的多,拿的大,可赢得几个“刮鼻子”……
我曾在《九月九,点蜡烛》纪念夏老师一文中写道:“春日里,晌午头,春风煦煦,阳光融融,夏老师领我到墙根下,叫我脱下棉袄,给我拿虱子。我靠着墙,晒太阳,心里暖洋洋。夏老师两个大拇指盖夹得虱子巴儿巴儿响,就像‘刀来米发’那样好听;不一会儿,指甲盖便红红的,好像染了鸡冠花,美丽又好看。”
再比如知了——它不仅好玩,而且还可以做“买卖”。正如先生所说:“他用两只‘钢虫’换来同学的一把卷笔刀,一块带香味的橡皮,想一想真是一桩不错的买卖。”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我捉到两只知了(一公一母),跟同桌同学(他是镇上书记的儿子)交换了一本无封面的连环画——讲的是小兵张嘎的故事。我如获至宝,因为头一回拥有自己的“小人书”……
《捉狐狸》,“据他们说狐狸最可怕的是伪装自己:变成美丽的姑娘去迷惑年轻人,或者变成别的什么东西,反正只要是祸害人的方法,它们都愿意试一试。”那么,“狐狸在哪儿?大家会说一定在林子里。这是不会错的,它们主要是在那里,因为喜欢树。”
俺庄周围有很多树林,但曾未见过狐狸。倒是黄鼠狼(也称黄大仙)却是俺庄的常客,有时一群一群的,极像过境的日本鬼子。记得有天傍黑,有支“队伍”来到俺家,把一窝20多只鸡鸭鹅统统掠走了。俺一家人却不敢吭一声,眼睁睁看着它们越墙而去。据白胡子三爷爷说,这些黄大仙惹不得,如果冒犯它们,就会施展妖法,弄得你神经错乱,整天说胡话。
再后来,还听白胡子三爷爷说,西河崖树林里住着一只成了精的“黄大仙”,谁人都怕它。可是,邻村有个号称“铁夹子”的光棍汉,就是不信那个邪,非要跟“黄大仙”较量较量不可。那年冬天,“铁夹子”瞅准了“黄大仙”的活动路线,在西河崖布下10只铁夹子,不知“黄大仙”麻痹大意呢,还是行使“苦肉计”,反正它被夹住了,而且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真像死的一模一样。“铁夹子”猫在荆棵里,老远望见捉住了“黄大仙”,便顶风跑过去,快到“黄大仙”跟前时,它一个鹞子翻身,站立起来,翘起屁股,朝着“铁夹子”放出一阵阵臭屁,“铁夹子”不一会便晕眩倒地,“黄大仙”乘机过去,一口咬断“铁夹子”的喉管,便一命呜呼了。“黄大仙”趴在地上,稍息片刻,狠狠心,一口咬断被铁夹子夹住的腿,而后舔舔伤口,很快痊愈了。据目击者说,“黄大仙”化作一条金线飞进了西山密林里……
《笼中鸟》里面说:“去哪儿弄鸟?最方便的是逮几只麻雀。夜间用手电照到屋檐下的麻雀,它傻傻地转头,就是不飞,被我们乖乖地捉住,塞进鸟笼里。可惜它们不会唱歌,还特别爱生气,水米不进,眼看活不了几天。”
儿时,夜黑天捉麻雀,我们也很拿手;听白胡子三爷爷说,麻雀都是“夜盲眼”,所以手电照到它们,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每晚捉个十只、八只不成问题,回家将其毛拔干净,开膛洗净,油锅里一炸,香的不得了!
可是,白天要捉只麻雀就不那么容易了,见人老远就飞了,所以菜园里、谷地里都插着稻草人,就是吓唬麻雀的。后来,听白胡子三爷爷说,麻雀是被“灭四害”吓破胆了。
大概是吧?外国的麻雀好像没有“恐人症”。那年到俄罗斯旅游,我们来到莫斯科“金环小镇”,这天下着小雨雪,那些和平鸽子随着人群飞舞,如同天使般与你亲近,即便是麻雀也不惊不乍,似乎也在与人为善……
过了几年,我们又去了瑞士小城卢塞恩,那天午时,我和m君坐在湖边条椅上,吃着自带的干粮。不远处,有两个金发少年,掰着面包,引逗着麻雀们;它们飞将过来,啄食着少年手上的面包,并扇动着快乐的翅膀……俺俩虽然老态龙钟,但觉得这里的麻雀忒可爱,也学着少年的样子,用山东煎饼引诱着;它们一点也不见外,纷纷飞将过来,争食着山东煎饼——我揣想,可爱的瑞士麻雀,你们及你们的祖先肯定没有摊上我们中国那场“灭四害”战役,使得你们可以与人共舞,与人为乐……说到底,这也是人类的福气。
综上三文看来,张炜先生对动物情有独钟。在《爱小虫》里,一会儿对小虫子深表同情:“大人往往讨厌它们,一见就驱赶拍打,有时还有喷洒农药”;一会儿又质疑自己:“我们这些人长大了也会像他们一样吗?”不会的!因为“这世间凡是最好的东西总是少而又少的。”所以,“我爱小虫!”进而,张炜先生在《捉狐狸》中大声疾呼:让“我们像动物那样热爱大自然”吧!不过,张炜先生对《笼中鸟》有种悲悯情怀,最终“把笼中的大鸟放掉了。”
是啊,关爱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善待动物,也是善待人类自己。
(二)
《粉房》,是我们儿时最诱人的地方,也是最神奇的地方。“一口大锅,里面是沸滚的水;锅的上方立了高高的木架,上面坐了一个挥拳的大汉,他不停地呼叫,一边叫一边狠狠击打一个有无数洞眼的铁桶,里面就流出细细的粉丝,它们缓缓落进热腾腾的锅里——一个人伸出长长的大竹筷子,不停地将粉丝拨到一旁的冷水缸里——几个姑娘飞快地用竹竿串起缸里的粉丝,唰唰地挂到木架上……”
俺庄下粉条是在饲养院里,这里有口“十八印”的大锅,那是“吃食堂”时候留下的。俺庄下粉条一般是在冬闲的时候,而且大多数是在晚上,白胡子三爷爷说,夜深人静,粉条下起来顺溜均匀,吃起来才有嚼头也更筋道。其实,他是为自己找借口,因为白天他得铡草喂牛,煮食喂猪,只有伺候好了畜牲们,晚上他才有闲空。因为操控粉条“漏瓢”很有门道,只有他游刃有余;他下出的粉条不仅粗细适中,而且像瀑布顺流而下那样好看。
我们最爱看白胡子三爷爷下粉条了。他光着膀子,站在锅台上,将连接漏瓢粗粗的麻绳套在左胳膊肘上,将10斤重的漏瓢端在手里,朝着滚烫的开水,用右手均匀敲打着瓢沿,一条条雪白的浆液潜入锅中,另一人见够一架了,便用长筷子割断,如此反复来往,一瓢粉团大约能下十架左右的粉条——到了最后那瓢,白胡子三爷爷总会留下一些粉团,用手圆出团圆,丢进锅里,熟了亲自用笊篱捞出来,分给躲在门口看热闹的我们,一人一个,不多也不少——其实,白胡子三爷爷在下粉条的劳作中,早就瞄好人头了……
我们来时就商量好了,今晚都跟白胡子三爷爷睏在一盘炕上。
《大清的人》,“他脑后果然有一根细细的小辫子。我差点叫出来。太怪了,这小辫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一拇指那么细,又干又涩像一绺枯草。”
俺庄也有个留长辫子的男人,都叫他阎老大,接连“乡试”不少回,就是考不中,连成家也耽误了,一直是条光棍汉,但背后有人说他是“儿异子”(两性人),意思是说他不男不女。别看他其貌不扬,但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祖传郎中,还能掐会算,既能悬壶济世,又能普度众生,因此托在他身后的那条长辫子就不足为怪了。
有一次,我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出其不意揪住他的长辫子,就像拽着黑犍子尾巴那样使劲往后拉了一下,不知怎的,他那么没有脚跟定力,一腚坐在地上,吓得我撒腿跑了。我拐进墙角偷望过去,他一个劲地抚弄着长辫子,就像爱惜他的生命一样……
白胡子三爷爷知道我惹了祸,便带我去向“阎爷爷”赔不是。阎老大见白胡子三爷爷亲自登门拜访,高兴地不得了,又是倒水又是端出炒花生,还抚摸着我的头说:“不怪孩子!那个朝代是该亡啊!根基有病了。”
是看在白胡子三爷爷的面子呢,还是因为他的长辫子丝毫未损?我不但没有受到责怪,还得了一捧炒花生。
《打铁的人》里面说:“所有的营生都好看,有时甚至不差于看电影。”这就是打铁人的故事。其行头“打铁的装束和常人不同,……他们干活时扎一块黄布油裙,有时脚上也扎一块。通红的铁块夹到砧子上,一锤下去火花四溅,一团团落到脚上,冒着白烟。这些人最少需要三人合伙才成:拉风箱的、抡大锤的、掌小锤的。谁的锤子小谁就是老大,人人都听老大的。……他们个个力气忒大,不说话,只干活。”
我们乡里会打铁的只有三帮,他们都有固定的村庄,好像早就画好了地盘,井水不犯河水。每年农忙时,来俺庄打铁的是山里坳人,姓胡,亲兄弟三个,长得就像一个模子卡出来的:“……平头,黑脸,红眼——这是火眼金睛。这种眼与别人不同,能看清煤火里的铁。”胡老大执小锤,胡老二抡大锤,胡老三拉风箱兼做下手,他们干起活来就像演一台大戏,好看极了。
胡老大见大铁陀烧红透了,便用大铁夹子夹到铁砧上,敲打着小锤,铮铮作响,很好听;胡老二往手心吐两口唾沫,随手抡起大锤,吹胡子瞪眼地砸下去,火星子四溅,怪吓人的;胡老三麻利地焖好炭火,也跟胡老二一样,抡起大锤,你一下我一下狠砸大铁陀,一来二去,三四个回合下来,便显现出农具的雏形,比如镰刀、镢头、犁耙什么的。而后就是细活了,胡老三只管拉风箱、掌好火候;胡老二随着胡老大小锤点到的地方敲打着,看起来很轻巧的样子……不多会就成器了,胡老大将它放进铁桶凉水里蘸几下,然后夹出来扔到地上……我们急着围过去一睹为快,狗剩还用指头戳了一下,随即烙出一个燎泡,吓得我们后退了好几步——没想到,打铁的这么厉害!火星子一个劲地在身边溅着,也不见一点伤痕,难道他们也是铁打的?——因此,我常在梦里央求着:“三位大爷,行行好,给俺打把手枪呗!”
从以上三文依稀看到,芸芸众生,纷至沓来,各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活剧。《粉房》里柴火熊熊,蒸汽氤氲,七八条大汉上下其手,将一团团淀粉演绎出美味可口的粉条。《大清的人》看似古怪,但不乏性情中人,既能悬壶济世,又能普度众生,可谓“恬适人生”。《打铁的人》更是一手绝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锤起锤落,敲敲打打,锻造出各等农具家什,让农民兄弟去耕耘希望的田野,年年充盈国库粮仓……
人啊人,才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
读《张炜文集》随想相关文章:
★ 东北行之一
★ 梦里水乡
★ 农民真幸福
★ 老宅的松柏树
★ 北湖的四季
★ 丑石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