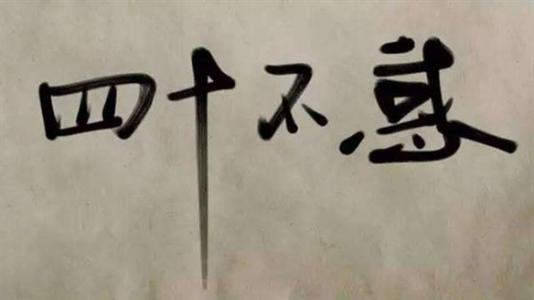石砚塔是我见过的陕北高原上最孤独的地方,历经了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自然灾害,那么多的岁月,那么多的风霜雨雪的洗礼,这个古老的村庄,依旧守着那片黄苍苍的天穹,贫瘠如荒漠的土地。一座座蓝灰瓦顶的土坯房,抱团取暖似的簇挤在一个山窝窝里。这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留给我的深刻的印象。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的时候,来自大都市的人像一阵飓风,扑涌向这里。因为在这块表面荒凉的土地下面,蕴藏着无尽的石油、煤碳和天然气。
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小村庄。记得那天格外的寒冷,我从包头转乘的火车在一个叫大柳塔的小镇终止了它的行程。出了火车站,在大柳塔镇那条不长的街面上,来回转摸了大半天,就是找不到一辆开往我的目的地——石砚塔村的交通工具。都说我的老家闭塞,哪知天地下还有我们比不过的?惊异之余,我感到万分的沮丧和无助。
眼瞅着日头快要落掉了,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加上天更加夺命的冷,可让人咋整?正当我焦急无奈的时候,突然一辆摩托车停在我面前。“大哥,看样子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来这地方找人不是做什?”声音是从骑在摩托车上人的厚厚的围巾捂着的嘴里冒出来的。这人头上戴一顶狗皮棉帽,身上穿着一件羊皮大衣,丝丝地散着膻臊的气味。“嗯,嗯,我要去石砚塔的矿上,可大半天找不到一辆车,我是头回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您知道去哪能达个车?”
“大哥,看来你还真的不知,我们这地方僻静,你说的石砚塔更偏了,还车呢?一条像样儿的路也没有哩。要不你看这样行不,天黑路不好走,你给上我五十块钱,我捎你去咋样?”他的话听起来像把刀,有血淋淋宰人的气势。
尽管我心里犯嘀咕,可天黑地冻,还能有啥招数?“那太好了,太感谢您啦?”我拧巴着硬从嘴里挤出这么一句应承的话。
“好说,大哥,你上来坐稳了哇。”
“突、突、突”,摩托车干叫几声,后轮胎扬起一股沙尘,便驶入一条上山的小路。这条路真是人经常走过的?车子时而扬起头,时而俯下身,坐在上面,仿佛坐在一艘顛簸在惊涛骇浪路中的小船上,我周身的筋随着颠簸一阵赛一阵的紧抽。摩托车的远光灯映出的光影中,一株株枯干的沙枣树,黑魆魆的,闪着深蓝色的磷光,像飘飘荡荡的鬼影,透着阴森森的寒气。忽而被惊起的小动物,奔逃时作响的“唰唰”声,让人头皮发紧,身上的冷汗扑沙沙的。摩托车在崎岖坎坷的小路上痛苦的挣扎着,呻吟着,而这呻吟声和着夜籁中各种响动像一波波卷起的重浪,重重地砸碎在夜的礁石上,越是往山林的深处,这支交响乐就越奏的响亮。
两个多小时惊惧的行程,随着摩托车滴溜溜滚下最后一截山路岗,远处隐约忽闪的灯光中终于要结束了。我们面前突地跃出一带很宽的河床,车灯掠过的地方,不见半星冰的踪迹,统治河床的是漫漫的绵沙,一截截枯树的残尸七零八落地横躺在沙土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脑海中不知怎么就跳出这一句来。“吱勾”,摩托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骤停在村口的一个小客栈门口。
“大哥,到了,这就是石砚塔。”客栈也听见了这件尖叫,忽闪一下,窗口流出了一股亮煌煌的灯光,光影里,骑车人的睫毛上鼻孔处闪烁着亮晶晶的白霜。
“五十块钱少了点吧?”我的话中那股浓烈的愧疚的味儿差点呛了我一下。这就是陕北人啊,地地道道的淳朴憨厚,我在内心狠狠地责骂了几声自己之前的歪想与猜忌。
“够了,够了,只有多没有少,那我就见你钱了昂,大哥,你远路风尘的,赶紧进去暖和暖和,早些缓着去,我就不打搅了,走了昂。”话音还末落瓷实呢,摩托车已转身“突突”地远去了。天鹅绒般的夜色里,一个红色的光点越来越远,越来越含糊,最终消失在山林里,消失在我潮湿的模糊的视线里。
开店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自称赵怀树。一进屋,他忙不迭声地喊婆姨给我端来两盆热水,一盆洗脸,一盆烫脚。洗涮完后,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速冻饺子就上了桌。老赵憨笑着说,“没啥准备,你就凑合一顿吧。”后来我才知道,速冻饺子是他们店里最好的吃食。饭后我被带到靠里屋的一个小房间,一具火炉,一面火炕,简简单单的。可能是真有点儿累了,也可能是心放下了,一躺在热腾腾的炕上,我浑身的血就开始汩汩地舒服地流动,疲惫蜷缩在我的身体内,促成了我快速的入眠。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便向老赵打听了杨矿长的住处,他口里一边说着“杨矿长啊,这人我知道”一边打发他小姑娘秀娥把我领往沟沟对过的那排新建的平房。
杨矿长已经等在沟沿上,八成是老家那边提前打电话过来通知的吧。“小周,你来了,辛苦,辛苦,我这两天已叫人把你的住处拾掇好了,就在那边,右手第二个房间,你先进去看咋样?”说完他又忙去了。我没有马上进去,趁着早晨的阳光,我得仔细把这周遭打量打量。
朝霞刚在山岗上空染上一抹红晕,白刮刮的大地已抹去了浓重的夜色,等待着第一束阳光的普照。石砚塔村,罩在一团寒冷的雾气中,有几家烟囱张开的嘴巴,已吐着缕缕的蓝烟,漫上沟沿的晨风,刺的人脸颊生痛,远处山脚下开工的机械,传播着隆隆的涛声,断断续续的炸药的爆破声,撕碎了这山村的宁静。那条昨夜首先迎接我的河床,并不完全那么空旷,各种大小不一的运输车辆,扬起的尘幕让它有了几分生动。嗯,这往后的一年,我要生活在这个模样的地方。
我来这个矿上,没有什么具体可要做的事,也没带着个人的目的,我只是替别人雇来的一双眼睛,所以,在我呆的那段日子,几乎见天的在石砚塔村里晃来荡去。有时停足在几个抽着烟杆老头们身边,听他们山南海北地扯着闲磨,有时立在一群扮得花花绿绿的女人们的边上,看她们热情似火地扭着秧歌。做为一个外来人,怎样才能不被他们当作一个入侵者而与他们古朴而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
石砚塔,从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任何追求进步的征兆,这里的人们,严守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老的生活传统,全然沉浸在一种压抑的平静中。当别人恣肆地掏腾着他们祖辈生存的这片土地下巨大的宝藏,他们浑然无动于衷,就像局外人一样,摆出一副此事与我何干的姿态,那种本应该做出立即起来保护的反应,始终深埋在他们与世无争的麻木的表情下,我为这种漠然感到不平,感到痛心!
难道几千年贫困与落后的压制,使他们习已为常了?还是生活的苦难炼就了超乎想象的的隐忍与耐心?眼见大开发的巨轮已驶到他们身边,但他们并没有上船的意识,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已成他们唯一而不朽的宗教信仰?村庄与矿区仅隔一道沟壑,却如一条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把这里乡土生活的淡定和外界财富争夺的激情划分的如此分明?我清楚地认定,这两方将任何一方都视为完全陌生的世界!
佝偻了千年的古老村庄啊,也该到立起身子的时候了!也该到觉醒的时候了!
陕北的太阳和风,是最杰出的塑造沧桑感的艺术家。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两个月,我的城里人的那种神气被剥蚀得一干二净。古铜色的皮肤,浑身的土气,让我不带半点儿异样地完全地融入到了当地人的队列之中。尽管石砚塔与我的老家相隔千里,但我们的根都深扎在这块黄土地,我们各自身上所带的那种固有的纯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同质。
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从穷山沟爬了出来,见识了更加文明先进的社会。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有一种责任和义务,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产生一种渴望美好、创造幸福的动力,这也是我焦地等待着尽快发生的事。我借着一切可能的机会,把我的所见、所闻、所知,生动的讲给他们,慢慢地,爱听我故经的人多了起来,甚至还有人约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我从他们从初娌试探性的感兴趣再到急切的想知道的微妙变化中,预感到了将要来临的事情。
石砚塔村落不大,村里读书的孩子也稀稀拉拉的。从三年级起,孩子们就得到大柳塔镇就读,因为交通不便,必须住宿。由于自己闲时间很多,我几乎转遍了每家每户,乘着周末和假期,我把所有上学的孩子动员召集在村子的小学堂,组织他们学习。我在高中从教多年,像初中语文、英语,小学数学还是能应付得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的娃们并不似大人们那般保守自闭,他们对我组织学习这件事很有热情,很是积极。相处熟悉了,他们也大胆地向我表述了对未来充满稚气的想象和憧憬,还有对外面大世界的渴望。他们和城里孩子没有什么过大的区别,只是地域环境的落后无法给他们安上放飞的翅膀。看着孩子们对我的真诚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我有了一种莫名的责任的沉重,开始白天黑夜地编写讲义,把各科的基础详尽地整理汇集,力求使演讲生动有趣且便于理解记忆。那一年与孩子们相处的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充满”崇高气概和慷慨精神”的日子。后来,过了几年,我陆续收到了一些孩子的来信,信中除了他们对我表达的感激和思念之情,更令我欣喜的是,像白雪洁、郝艳萍、赵秀娥等好些人先后都考上了大学。
二十来年过去了,我再没回到石砚塔去。不知那里现在变化的情况,只是从别人的转述中了解到,村民们已介入当地的矿区。听说每个矿每年都得给村民们分上一定数额的红利,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也参与了矿区的开发和管理中,这的确都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我们的幸福,并不完全与别人毫无关系。时光终归会让我们走在一起,人类命运的休戚,不是哪一个人能独立地扛起,而是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共同来承一担。
党的退耕还林的政策,想比也泽福于陕北那偏僻的一隅之地,那片被太阳去大风晒如沙漠的黄灿灿的土地,如今也许有了自己繁花盛开的季节,也已披上赤橙黄绿的外衣。
“青山绿水”的浩浩春风,一定催生了我期待已久的来临!
石砚塔,只要你愿意,我一定择机去把你看望!
石砚塔相关文章:
★ 东北行之一
★ 梦里水乡
★ 农民真幸福
★ 老宅的松柏树
★ 北湖的四季
★ 丑石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