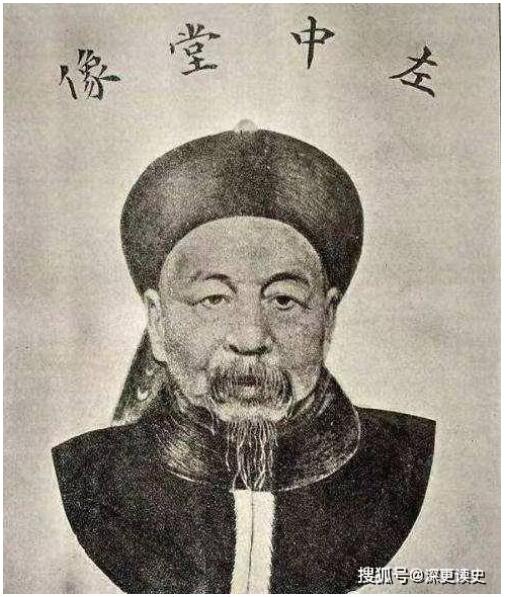我有一个老物件,跟着我整整二十年,其实也很普通,就是一条毛巾被。
当年到武汉读书时,父亲非要亲自送我,态度也是非常的坚决,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出过远门。
启程的那天,天刚朦朦亮,坐上二弟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从安徽泗县小姚庄,一路曲里拐弯地来到灵璧县冯庙镇,然后转乘一天一趟的长途客车到达江苏徐州,又从徐州坐火车到了湖北武汉。
那是一趟慢车,我的记忆中是二十三个小时,坐的下肢都是肿的。
只是单趟,就花去了我们爷俩两天多的时间。
九月的武汉,酷热难耐,暑气蒸人,果真是个火炉城市。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父亲准备返家。
临别之前,离发车的时间还早,我依依不舍地和父亲漫步闲逛,从武昌的蛇山这边,走上武汉长江大桥,顺着人行道,走到汉阳的龟山,然后又从龟山返回蛇山。
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桥下火车轰隆隆飞驰而过;江面上沙鸥翔集,江水中轮船缓慢行进,不时传来几声鸣笛。
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跟我之前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而且离家还那么的千里遥远。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看得出来我对未来生活的忐忑和期许,总之是反复不停地安慰我嘱托我,让我不要牵挂家里,不要想念家人。
父亲一再强调说,如果手头没有钱了,就给村里有电话的邻居家里打电话说一声,或者是及早地写信告知,反正是不得短了我。
其实,我知道,为了我到武汉念学,家里能变现的,都已经卖光了。
奶奶养的羊,妈妈喂的猪,弟弟打工挣的钱,屋子后头的杨树,以及父亲给别人家耕地打场拉石头攒下的钱,都被父亲交给我了。
农村的孩子,上个学真是不容易。
除去已经交过的学费,还有给我的未来几个月的生活费,父亲的身上所剩无几。
但是,父亲经过默算,又给了我二百块钱。
“没有想到武汉这么热,这点钱你拿着,回去找个商场买床毛巾被,不能给热着,也不能叫冻着。”
我推让着不要。
“别犟!我已经留够了回家的车费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家里地里什么都有,我们在家里,总不得饿着!”
几番推辞,终拒绝不得父亲的固执,我接下了父亲手中的钱。
父亲回去的时候,没有买着座票。
我知道,父亲是一路站着,间或是在车厢的交界处坐着返回了家。
我终按照父亲的嘱咐,到学校旁边的商场里,买了一条毛巾被。
毕竟,这是必需品。
这条毛巾被,纯棉,淡青色,带着突起的阳花。
这条毛巾被,陪着我在武汉,度过了几年酷热的夏天。
这条毛巾被,后来又随着我碾转几个城市,至今盖了二十多个夏天。
这条毛巾被,已经与我磨合的非常的妥帖。
盖在身上,柔软舒适,薄厚适中,不刺不扎。
在解暑的同时,又能防止风寒,仿佛幼年时父亲摩挲着我的大手,总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每年夏天,我都会把它拿出来洗净,陪着我整个季节。
待到天凉时,我再把它洗净晾干收好。
不知怎的,对待这条毛巾被,我始终有着一颗圣教徒般虔诚的心。
二十多年,许多物是人非。
二十多年,初恋,梦想,以及其他若有若无的东西,走丢了,遗失了,遗忘了,抛弃了。
唯独这条毛巾被,虽然有些变色,有些发黄,有些跳线,但是,我一直敝帚自珍,视如宝物,舍不得丢弃。
每次盖着这条毛巾被,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父亲给予我的爱,以及呵护,即便父亲不在我身边,以及,不在人世间。
一条毛巾被相关文章:
★ 芦花飞舞的季节
★ 城里的月光
★ 乡宴
★ 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