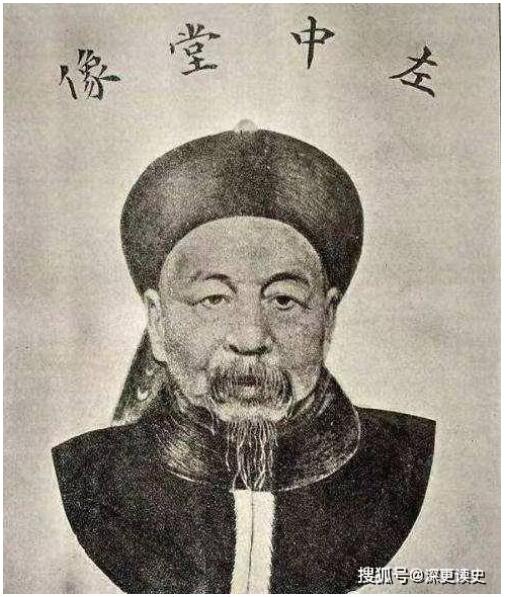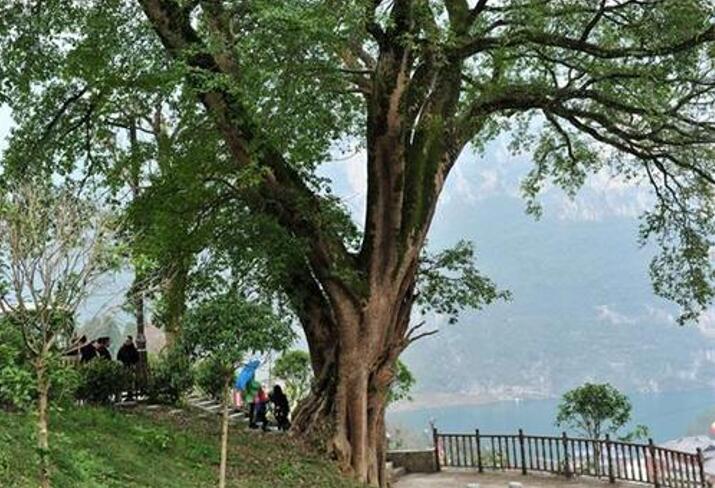母亲的三次教诲
刘海清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是,在母亲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她是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个年龄的村妇极少有读过书的,可是母亲出生于大户人家,读过五六年的私塾。所以,母亲的说话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至少我的感觉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母亲特别爱看戏,知道很多故事,我很少的时候,她就经常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力保大宋江山、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到县一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母亲慢声慢语却又是很严肃地跟我说:“你要好好地工作啊,别让国家白白地培养你一回!”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工作的!”母亲说这些话是有来由的,我是1979年上的大学,那时农村还没有脱离贫困,我大学期间的学费、伙食费都是国家买单的。
我在一中工作了四年,刚刚参加工作,万事开头难,我可是如履薄冰,不敢有半点松懈。教了两届高三毕业班,1986年,我所教的高三毕业班语文高考平均分获得全市第二名。
1985年暑假,我结婚了,妻子在另一个县当老师,结婚即分居,我们两地相隔三百华里。各自教学任务都相当重,极少见面,联系只能靠写信。
1987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调到了县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不当语文老师了,却管起了全县的中学语文老师,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既新鲜,又刺激,当然了也是个挑战。
这年,我二十八岁,已经褪去了稚气和年少轻狂,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母亲的话又萦绕在我心头,我到新岗位了,那就放手一搏吧!
三年后,妻子从另一个县调到我们县,我们安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家。
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到各个学校听课,检查,开展教研活动,举行各种竞赛,上传下达各种信息,同时也带有行政意味,还要配合其他科室的工作。
我所在的县地处燕山深处,也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域广大,山势高峻,交通极其不便,工作条件也是异常艰苦。我在教研室工作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段。现在,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23年了,还常常回想起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所经历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些难忘的事。说来也奇怪,连做梦都是那个时候的事。
那时交通不便,班车很少,路况极差。我到一所偏远的学校,要颠簸三四个小时。数九寒天,早晨四点就起来赶车。经常住在乡下。我遭遇一次车祸。那是一个春天,早春的微风仍然难以抵挡住山野间的寒气,农人们已经开始种地了。我下乡返回途中,班车沿着盘山公路开到半山腰,司机突然打盹,车子猛然偏出道路,往外侧冲去,人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几秒钟时间,车子突然卡在了路边隆起的小山包上,45度角倾斜着,往下一看,是个斜坡,足有七八十米长,坡底下是一片平地,三个村民正在种地。人们这时才慌乱起来,有的喊叫,有的大哭,我倒是很镇定,我高声喊,大家不要怕,没事的,从里侧车门出去,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这时我看到司机面如白纸,冷汗直流,腿都软了。几个女乘客蹲在路边,大口呕吐。我们庆幸逃过一劫,否则,车子翻下山坡,我们连同三个村民,后果难以想像。我至今还奇怪,当时是生死关头,命悬一线,我出奇地一点都没有害怕。过后,我的害怕劲不知不觉就来了,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很长一段时间,夜里老是做恶梦,有三年时间,我一坐上班车就恐惧得无法克制。
1990年12月底,我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一个中学检查,天下起了大雪,连下三天三夜,大雪没过膝盖,远处的山头就像一个个白馒头。回县城没有班车,我们一行三个人被困住。等了一周,积雪没有融化,我们急得火冒钻天。校长雇了一辆马车,要把我们送到县城。我是小组长,坚决否定,那样太麻烦。与校长一番争执,决定把我们送到离县城五十多里路的一条县级公路上,我们走回去。送到后,我们开始步行,路上积雪已被踏平。我们翻山越岭,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我们走到一座叫做王杖子岭的顶上,往西面看,红日斜挂,橘红色的晚霞映红半边天幕,群山巍峨,绵延无尽,大小高低的山峰在晚霞的映照下,似一簇簇红色的巨浪。好一幅苍山落照图!那壮观的景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到了岭下,我们在老乡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才到了县城。
有一次,我在一座距离县城很远且班车极少的相当贫困的乡镇中学检查,已经出来三天了。快吃午饭的时候,总校长赶来,说我妻子把电话打到总校,我上幼儿园的儿子从滑梯上摔了下来,受了伤,让我赶回,没什么大事。我当即就要走。校长说别急,吃完饭再走,回县里已经没有班车了,必须往西翻过两座山岭,到另一个乡等待外县来的过路车,大约四点半到。我草草吃了点饭就赶路,路越走越高,人家越来越远,我第一次走,道路不熟。看到路边一个六十上下的男人在干活,我想问问路,谁知此人直勾勾地看着我,啊啊地说着什么,手里比划着,原来是个哑巴。我们这里的说法,出门问路问到哑巴身上,是相当不吉利的。我苦笑了一声,继续赶路。晚上七点多到家,儿子额头上缠着绷带,破了一个口子,伤势不重。我连吓带累,急火上攻,发起高烧,连夜住院。
我一次下乡整整一周,周末兴冲冲地回家。到门口看见妻子正在泼水,我说我回来了,妻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一句话没说。这是怎么了?我进屋才看到,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中间的隔壁墙塌了半边,满屋砖块,泥土,砸坏了大衣柜等家具。妻子没好声气地说,你走后就塌了,你再不回来就可能把我们娘俩砸死了!什么也指不上你!
我在教研室工作的十年,所吃的苦,受的累,遭的罪,一时无法诉说,真有些不堪回首的感觉。尤其是遇到几起突发性的、意料不到的事,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有几分危险。比如,我在长途车上被地痞推搡,在下乡途中的班车上被醉汉刁难。我在城市公交车上被偷,好在损失不大。我在城市广场,被人用假金戒指企图行骗。我在火车站,被小商贩强卖。我在宾馆住宿,半夜被失足女纠缠不休,我最后说我是警察,你再不出去,我把你铐起来。我也曾几次想换工作,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科室,喝喝茶,看看报,舒舒服服,拿着薪水。但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母亲对我的殷切的教诲,我立即打消了离开的想法。感谢母亲,让我咬紧牙关挺过了这十年。
1999年,我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了九年之后,妻子调往省会,12岁的儿子随母南迁。从此,我又开始了漫长的不知何时结束的分居生活,天长路远,云山阻隔,相距整整一千二百华里。我因为弟兄一人,照顾父母,留在老家,当时母亲已经身患脑血栓,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一天,母亲坐在板凳上,佝偻着腰,用不太清晰的话语跟我说:“你到这个岁数了,还夫妻分居了,不要因为我们,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家庭,都怪我们,拖累了你。“母亲似乎有些话还要说,硬是打住了。我有些吃惊,母亲怎么说起了这个?知儿莫如母,母亲是理解我的,有些话她没有细说,深说,母亲的话里明显有着担忧,妻子和儿子毕竟远走高飞。让我倍感不解的是,母亲这个时候还把我的工作挂在嘴上,不忘告诫我要好好工作。她这样的农村老妪。老眼昏花,弯腰驼背,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哪来的这种境界?啊,啊,是我错了,我看错了母亲,低估了母亲,与母亲比起来,我倒显得有几分低俗呢。这到底是我的母亲啊!流逝的岁月和老病的身躯,并没有改变我的母亲!
我很快离开了教研室,带着评中学特级教师的美好理想去了一所中专,按说,从教育“衙门“机关出去的人,应该名正言顺地担任一官半职,我没有考虑这些,一头扎在教学第一线,担任两个班的课。我每周12节课,还要看三个早晚自习。学校管理非常紧,有严格的考勤办法和请销假制度。我只能五一、十一两个长假,寒暑假去省会,一年就四次与家人团聚。
我的讲桌前不断变换着新鲜的面孔,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这一干不知不觉就是多年。
近年来,许多同事看我年龄大了,劝我别再教课了,找个轻松的岗位待着吧,我婉拒了。一个与我关系很要好的同事,同时也是个作家,好心好意跟我说:“刘老兄,很多比你小好几岁的人都不教课了,你可以去阅览室、图书室做做管理,一来没有压力,一来可以满足你读书的愿望。”我说,很多同事都这么劝我,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真的不想离开课堂。我永远忘不了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教诲我的话,我不好好工作,就觉得有悖于母亲,对不起母亲。同事大笑:“真书生也!“
2012年8月,母亲脑血栓并发肺性脑病,心力衰竭,身为医生的二姐每天来家里给母亲输液,持续十几天不见好转反而一日不如一日。二姐跟父亲和我说,母亲怕是大限已到,让我们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母亲已经不能起床,饮食靠喂。母亲本来就瘦小的身躯好像又萎缩了一圈,母亲盖着被子,躺在那里,满头花白的头发就像一团乱麻,满是皱纹的脸黄中透黑,整个人显得没有一点生气。我看一眼,就难受得吃不下饭。母亲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神志有时不大清楚。一次,母亲很明白的样子,神态也安详,她把我叫到身边,看到两鬓斑白的我,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神采。她跟我说,她知道自己阳寿已尽,但不怕死。她死后最担心的就是我,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也快到老年了,家庭还处于分散状态,她要我多往省会跑跑,不要心疼路费。她又说,我工作上不能松,我是国家的人,就得为国家尽力。越是到最后越是要干好工作,将来退休了也不后悔。说着,伸出枯树枝般的手,哆哆嗦嗦地从褥子边拿出五百块钱给我。我接过钱,跑到后院,差点哭出声来。我真想爬到南山顶上,哭得山摇动,树点头,云颤抖。我可怜的母亲啊,她自己已到临终,她生命的钟摆每时每刻都会停止,还这样惦记我,嘱托我,教诲我!
2012年9月12日,草木依然葳蕤,天空依然朗洁,但仍让人感到秋风的阵阵凉意,这一天,母亲去世。我请了一周假,安葬了母亲,我擦干眼泪,带着疲惫至极的身躯,继续上课。
2017年,我患上了一种顽症——末梢神经炎,两只脚底麻木,双腿膝盖以下像两个铁箍箍着一样,两条腿感觉就像两根木棍一样僵硬,一度走路、上下楼都很困难。我遍请中西名医看病,经过长时间的系统治疗,外加针灸按摩,才得以缓解,但此病目前尚无根治办法,且极其顽固,时好时坏,并不稳定。
即使这样,我步履蹒跚着依然给学生们上课。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我很难站立着坚持下来,有时候,实在坚持不了了,就扶着讲桌站一会,或到空位上坐几分钟。上完课后,我满头大汗,眼冒金星。书记校长我们是几十年的同事,多次让我请假休息,我硬是没有答应。我因为三次外出看病,有请假条,按考勤制度规定,年终还被扣掉了三百多块钱绩效工资。有时候,我也想,我何必这样自己与自己较劲呢?身体状况既然这样,不任课也完全在理。可是,不任课,我去哪里?拿我这个比较迂腐的书生来说,不教书其实就等于什么也不能干了。我一旦无事可干,工作为零,不就违背了母亲对我的期望吗?母亲去世才几年,我还没有从丧母的悲痛中完全走出来,就辜负了她老人家的愿望,我跟自己能说得过去吗?
学校很大,有三百名教师,自然了,有很多事,免不掉众说纷纭,众口铄金。同事们,特别是彼此缺乏了解和交流的同事,对我有两个不解,一个是我临近退休,依然在任课;一个是我天天读书,总往阅览室跑,一摞一摞地抱着书刊。这个习惯确实如此。我本身是省作协会员,业余一直坚持创作,经常有文章发表在各级报刊,我平生只爱读书写作。我校教工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在一起,负责管理的是八位清一色中年女老师,她们对我是格外的尊重。但是,时间一长,我明显感觉到她们看我的眼光似乎总是怪怪的,我并没在意这些。一次,我与一位沾点亲戚的管理员说起这事,她说:“姐夫,我们都不大理解你,这么大岁数了,老婆也不在身边,天天看书学习,究竟有啥用?你这个岁数的人,都在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姐夫你何必太苦了自己,太对不起自己了?”我哈哈一笑,说了一句:“我就是这个命!”其实呢,她们哪里知道,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背后,与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20年春节刚过,我再有一年就退休了,按学校的规定,离退休剩一年的老师,可以不上班了。加之疫情笼罩,我被困在家中,每天看书,写作,累了就去爬山。没有了工作,我倒很不适应,感觉心灵缺了依傍,情感缺了归属,力量缺了倾泄。我有些心神不宁,浑身上下,很不自在。
2020年7月,我应聘到县实验高中,负责宣传工作,主编一报一刊一号(公众号),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又焕发了青春,年轻了二十岁。虽然没有任课,但是每天与老师和学生打交道,依然与语文教学密不可分。实验高中刚刚成立,宣传工作还处于空白。每天组稿,看稿,采写,编辑,校对,操作,外联……忙得不可开交。
早晨,清新而硕大的朝日被大山的巨手缓缓托出,第一缕曙光瞬间洒遍山峦林壑,我骑着山地车快速驶向十几里外的新校区。傍晚,柔美而沉静的夕阳用她温润的嘴唇亲吻西山之巅的时候,我揣着一天的收获和满身的疲惫,踏上回家的大路。
我为教育事业工作了三十八年,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做到了问心无愧,当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首往事,心中没有遗憾。
究其原因,一个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也好,一个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读书人的道义也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的良知也好,一个深受国恩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感恩也好,这些固然都包括在内。然而,三十多年里,母亲的三次让我刻骨铭心的教诲,它们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是我几十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念源泉,是我几十年不断坚守的精神动力,是我几十年面对艰难困苦的意志支撑。
刘海清,河北省秦皇岛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河北作家》《河北文学》《当代人》《秦皇岛日报》《南方散文》等报刊,入选《当代华语作家文选》、《当代作家散文卷》,文学评论在《名作欣赏》《阅读与写作》《中国教育报》《中学语文》等6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曾获2021年、2022年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
母亲的三次教诲相关文章:
★ 芦花飞舞的季节
★ 城里的月光
★ 乡宴
★ 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