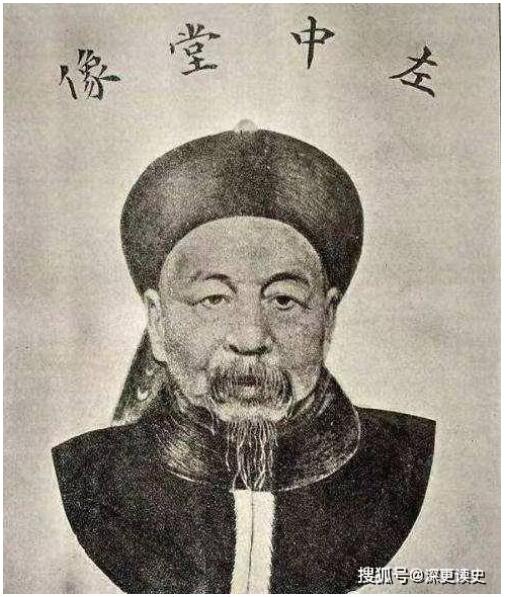《雪》
南方的雨水和空气一般,已将人的生活淋得透湿,彻底反复的冷反倒不算冷了。只有另一种冷,对南方人来说惹欢喜,讨亲近,乐意把全身洗刷一遍,那就是雪。
发掘珍藏一样,无论是远观百余里外山峦裹上的一顶白帽,还是凑近凝视咫尺内随手捉来的一只精灵,它都白得纯粹,柔得纯粹。可它却不甘纯粹,想方设法地澎湃人们心间的久违,沸腾想象的奇妙。那帽子不敢驻足了看,怕看着看着化成了一座座白色房屋,盘踞错落在远山上,添了一份人为的热闹。沙漠里的海市蜃楼,雪也善于建造。它也不拘纯粹,刚烈之傲蕴藏在这小小身干里。那精灵不敢狠劲一捏,怕捏到它的底线、它的软肋,迸发出十足的骨气,立即变得硬朗起来。说它娇柔,确实比花瓣还轻盈,不像从天上掉下来,像是从地上被不经意的风卷起来的,但柔里带坚,不容亵玩。说它多姿,确实能和孔雀媲美,没有固定的姿势展现在眼前,变化的同时更没有一丝刻意的做作,但美中有度,自然天成。
如此特别吗?在南方特别得见不着缺点、杂质和暴躁的恶行。如此干净啊,和我的心绪随这份干净、和净浓成纯白色,要么被小孩子随意揉作一团丢了去,或是在高僻的山岭上独姿漫舞,尽管无人观赏,也幸好无人围拥;不然便皑得盛大,莹得磅礴,迢迢奔去着,砸破秦岭淮河坚硬的阻挡,却在南方这片向来湿润平阔的天地间,乖乖驯顺起来,飘落一场温柔纤巧的、澄澈透亮的雪。静静铺满潮漉的泥土,簪上垂头的树枝,卧在斜展的屋檐,抱住断续的栏杆,无论什么材质,哪个去处,何种境遇,都处世不惊,安然入眠,犹如深谷里朵朵幽雅的兰花。
但雪也是灵动的,并非一举一动皆入“南”随俗,就像江南美人没有把温儒尔雅灌满整个水乡,多少也会向捣不完的衣裳直泼一瓢子水泄愤,或者和情郎互逐嬉笑在青瓦街坊。尚留着在北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血性,有时跟着泥泞滚下山坡,拌着土壤的黑色,伪装成灰不溜秋的脏女孩,只想畅快地赶山一回;趁时间稍稍出神,便独自挣脱高悬的枝头和屋檐纵身一跃,跳到充满未知的大地上,明知疼却不曾憋出一声哀嚎;也不和栏杆相厮相守了,宁愿抛往路边流离失所,一心投身在对自由的追求里。一片雪,一场雪,一个天地里所有的雪,都可枕上一个冬天的安详,也可以戏出春天才有的热闹。
北方的冰雪和空气一般,已将人的生活淋得透湿,彻底反复的冷反倒不算冷了。只有另一种冷,对北方人来说惹欢喜,讨亲近,乐意把全身洗刷一遍,那就是雨。雨是雪的母亲,雪是雨的女儿,听雨赏雪,它们的处处洒落都会被人接住,被南北方接住,被整个历史接住,盛进情思感念的容器中,荡漾丰富深绵的启迪、悲喜以及放松,而后继续听雨观雪,浸在雨雪霏霏的无言歌舞里高放人们的言行举止、百谈千绪。
天若有情天亦老,瑞雪弄春窗眠扰。
——夏爽
雪.相关文章:
★ 芦花飞舞的季节
★ 城里的月光
★ 乡宴
★ 春天的故事